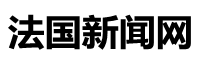本篇文章7702字,读完约19分钟
编者按:2018年除夕之夜发生的张扣扣案震惊全国,引发了舆论持久、广泛的关注。该案有哪些深刻教训?带给我们哪些启示?知名学者、文史专家、社会评论家邵光亭先生刊发署名文章,就相关话题进行深入阐释。
全文如下:
一、法治——文明时代的基本共识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时代,法律是解决一切纠纷的最根本途径,法治思维应当成为社会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全社会都必须深化对法治及其内在价值和规律的认识,实现从日常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变。
“依法治国”是鲜明的时代特征,公民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合法性为起点,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应当以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和法律逻辑为准绳。法治不仅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美好理想,也是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探索和实践得出来的治国理政、处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最佳模式。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法治建立在社会共同具有的理性基础上,反映社会成员共同的意志,经过严格的程序而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因个人意志和喜好而轻易改变,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它是人类向往和追求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类历史反复证明,法治是迄今为止人们可以找到的最佳治理方式。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需要与之相适应。任何违法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着力点。在当今时代,不应该对违法必究这个基本问题再有任何的怀疑与争辩。当前我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利益交织、矛盾错综复杂,带来社会震荡。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更加迫切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只有全社会都以法治来思考和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推动各项事业和人的发展。
二、任何行为都不能脱离法治框架之外
文明时代没有值得同情的恶意杀人犯,一切矛盾纠纷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任何法治框架之外的暴力行为都不应该被允许,更不值得鼓励和宣扬。无论以何种理由,任何以私刑结束他人生命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公权的制裁,这是文明的底线。
自古以来,基于不同原因的各种仇恨总是在在世间弥漫,而且往往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不断循环。个体、群体乃至国家,“以实现正义的名义”,常常被强烈的复仇情绪所左右且不能自拔,导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不断,甚至爆发战争。造成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悲剧,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扭曲、偏狭的仇恨心理不值得提倡,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需要我们从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
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往往与重大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法律与人情相互纠缠,但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坚持法律原则,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突破法律的防线。当权利受到侵害时,第一选择应该是寻求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传统观念的血亲复仇,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与法律制度格格不入。无论个人有多么充足的理由,都不能以私力报复方式解决问题,也不能以复仇的名义将他人自行处死!
美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摩尔根,把人类的社会发展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文明”是比“野蛮”进步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状态。在人类文明史上,围绕着应该实行人治,还是应该实行法治;或者说二者哪一种方式更优越,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和斗争。最终证明,法治取代人治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法治具有目的和价值的合理性,它所规定和追求的价值目标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公认的理想和观念。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社会成员需要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对所有社会主体而言,法治是社会处于一种秩序状态的最基本保障,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行为都必须由法律加以规范和调整。
三、中国社会“血亲复仇”的历史渊源
随着当今社会信息网络传播能力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中“血亲复仇”相关联的案件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关注,“为父母复仇合理合法”的传统宗法伦理,往往让一些人有一种错觉,以为“私力救济”可以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私力救济”的含义是——当国家司法救济来不及有效保护公民个人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允许公民个人采取自我救济的方式或方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刑法上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是不法侵正在进行时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私力救济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避免危害结果发生,因此,其实施的前提必须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如果是尚未开始,或者不法侵害已完毕,或者实施不法侵害者确已自动停止,就不再适用,否则仍然应当承担责任。现代法治社会,绝不允许公民个人随意采取报复手段来对他人实施暴力行为。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一直以来都有比较浓厚的复仇意识,这种意识也有其历史渊源。如《周礼》规定,为父母报仇不承担刑事责任。伍子胥为父兄复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为波澜壮阔的血亲复仇故事,历来为人们所注目,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过这个故事。
伍子胥(前559~前484)是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伍奢之子,名员,字子胥。鲁定公四年的吴楚之战,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伍子胥替父兄复仇。汉朝刘向《说苑•善说》云“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史记》记载:“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由于恩怨情感在人类全部情感生活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史上,复仇文学主题占有很大的比重,复仇情节成为作品结构最吸引人的内在推动力。尤其是涉及历史题材的作品,复仇是屡写不厌的主题。何昌淼《水石缘序》曾指出,“从来小说家言,要皆文人学士心有所触,意有所指,借端发挥,以写其磊落光明之慨;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即事奇、人奇、遇奇矣,而无幽隽典丽之笔以叙其事,则与盲人所唱七字经无异,又何能供赏鉴?”文学作品通过对某些主观情绪的渲染来实现作品的接受效果,这对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来说至关重要。复仇事件饱含奇趣震怖的因子,加上作品结构中挟带的英雄主义气质,可以让情节结构更加跌宕起伏,容易取得人们广泛的认同共鸣。
武侠小说作为汉语文学最重要的类型之一,更与复仇主题几乎不可分割。尤其是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它的公式化特征尤为鲜明:“一个孤儿——常常是因私仇遭到灭门之祸,以致流浪的孤儿,因特别的机缘,得到各种奇遇,包括灵丹、秘笈、动植物如鱼胆、何首乌之类、神兵,以及前辈高人赠予几十年、几百年功力,然后重归江湖,无往不克,赢得一大群美女的追求,最后则找到了仇人——罪恶黑帮的领袖,终能手刃寇敌,或晓得了身世真相。”武侠世界没有绝对的外在价值标准,容易烘托人物内心衡量恩仇时的矛盾冲突,配合古代野蛮粗犷的民风,更能表现快意恩仇的江湖变幻。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被血缘、宗法关系连接在固定而狭小的单位里,“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与外界甚至“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家国一体,君父合一”的国家体制,皇帝是封建“大家长”,是国家和臣民的绝对主宰。家长、族长则是一家或一族必须遵从的权威,这种社会基础必然生成专制制度。皇帝“受命于天”、“朕即国家”,权力私有,法律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恩格斯说阶级社会“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劳动人民只是义务主体而不是权利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分离,使得人们的权利很难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由于社会统治的不正常状态,“血亲复仇”便成为了消解社会情绪的一种渠道。
四、年深日久的“复仇”观念
武侠小说的侠义崇拜与英雄主义,反映了中国古代年深日久的“复仇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含有正义伦理的诉求,因此得到民间的广泛认可。通常情况下,复仇作品大多隐含着正义必胜邪恶的震慑力。无论是《史记•赵世家》所载的赵氏孤儿,还是后来的唐传奇,从《列异传》、《搜神记》的“干将莫邪”故事,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不管是鬼灵精怪超时空的复仇方式,亦或者侠义江湖,总之为了报仇往往是不惜任何代价,像伍子胥那样宁可破家掘尸也要告慰冤灵发泄仇怨。民间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志在必得,不避任何艰难地朝着最终的复仇目标努力。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一直有两大系统,一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礼乐教化经学伦理系统,一是民间自我调节系统。由于古代社会大部分人的知识水平有限,因此民间观念的形成,受以传奇、话本、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更大。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古代中国在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转型中,一直未能摆脱血缘宗法观念的束缚,这为血亲复仇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经学统治时代,礼法制度是两千年中国社会的主要治理结构,它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度之上,以儒家学说的亲亲观念为理论和道义基础。“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尽心下》)“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周礼·地官·调人》)自春秋战国以来,复仇一直就是中国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统治法与礼的矛盾。特别是到了汉朝,随着春秋公羊学派的兴盛,帝国政府甚至给予私自复仇者以法律上的支持。
在“以孝治天下”的标榜之下,在法与礼的冲突中,礼往往占据上风。唐前各代史籍所载,孝子烈妇为亲族复仇很少受到惩罚,被处死者更少。甚至还有下级官吏将报仇者处死,不但得不到赞扬,反而被上级官吏处死,这种事也屡有发生。谢承《后汉书•桥玄传》载,有孝子为父报仇被县令路芝处死,但齐国相桥玄竟将该县令“笞杀以谢孝子冤魂”,(见《太平御览》卷481。)。复仇行为往往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褒扬:比如沈充与王敦构逆,失败后被其故将吴儒所杀,他的儿子沈劲得以逃脱。后来沈劲为父复仇,灭掉吴氏一门,晋穆帝不但不追问,反而命之为将。
古代社会之所以有浓重的复仇观念,就在于:第一,手刃仇人的快感;第二,彻底复仇发泄心中的怨愤;第三,追求恩怨分明,毫厘不爽。对有恩者必酬,对破坏者决不手软。由于儒家礼制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千余年来血亲复仇文化的浸润,使得当代社会仍然对为亲人复仇抱有深深的同情。由此也可见文化传统的惯性。
五、复仇文化的悲剧特点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审美理想,总是崇尚“团圆”的结局。我们之所以要反对激烈尖锐的复仇文化,是因为其往往是酷烈的、充满悲剧性的结局。
血亲复仇,一般都是“敢于拼个鱼死网破的抗争行为”,往往伴随着血淋淋的屠戮,以生命的摧折为终结,造成极为酷烈的悲剧后果。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道德中关于有仇必报的思想,和“士为知己者死”、“重义轻生”的古代民间道德标准,是孕育这种悲剧的土壤。文学作品戏剧化渲染的古代复仇文化,寻求一种在酷烈、嗜杀、血腥中复仇的快感,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民族价值观背道而驰。
历史上,复仇是一个社会性的文化现象,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从未停止过产生影响。除了前面提到的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而对楚平王掘墓鞭尸,还有吴越两国的相互复仇,另外荆轲刺秦、聂政杀侠累、豫让杀赵襄子,魏晋南北朝时的桓温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沈休子、张景仁都在杀死父亲仇人之后以仇人的头颅祭奠自己的父亲,赵充在手刃仇人之后食其心肝。
更让人感到惊心的是,复仇情绪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创伤。《隋书•列女传》记载,隋代的王舜,七岁时父亲被王长忻夫妇谋杀,王舜与两个妹妹寄食于亲戚家,一直“阴有复仇之心”,长大后“持刀窬墙而入,手杀长忻夫妻,以告父墓”。《孝友传》记载,隋末的王君操六岁时父亲与乡人斗竞被殴杀,二十多年后,当时已经是唐朝了,王君操“密袖白刃刺杀之,刳腹取其心肝,噉食立尽”。《宋史•刑法志》记载,王贇年幼时父为人殴死,王贇长大后刺死仇人,将其头颅四肢砍下祭奠父亲……
除了基于血缘的伦理复仇,还有夫妻之间对不忠行为的复仇,妓女对负义背盟士子的复仇,以及国家复仇、民族复仇,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种种行为,已不能仅仅用惨烈来形容。
中国古代复仇文化强烈的悲剧性还体现在手段凶狠,对肉体和生命的戕害极为残酷,“其中有对被复仇者的酷烈,也有复仇者为了某种目的而对自己的酷烈”。比如先秦时期的豫让为了实现杀赵襄子的目的,“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聂政刺杀侠累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对仇者的酷烈则更令人发指:赵襄子灭智伯后,用智伯的头骨作酒杯;伍子胥复仇将楚平王鞭尸;晋代的赵充在手刃仇人之后食其心肝。而且报仇者往往杀戮殃及仇人的全家,《清史稿•王馀佑传》记载,清代的王馀恪、王馀严杀仇家“老弱三十口”,等等。唐代的周智寿和弟弟智爽为父复仇,最后智爽被判死刑。周智爽被处斩,他的哥哥周智寿为他收尸的时候,先是自残“顿绝衢路,流血遍体”,又“舐取智爽血,食之皆尽”,看到的人“莫不伤焉”(《旧唐书•孝友传》)。
“复仇心通常又是一种过火的动机;它追求越出适当分寸施加惩罚。”民间理念往往具有极端性、煽情性、煽动性和不可控制性,复仇意识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像野生的蔓草一样疯长。无论是哪种复仇,总是鲜血淋漓、尸体横陈,对肉体和生命的戕害极为惨烈,没有一点温柔敦厚的姿态。像元曲里的唱词所说的“钉上木驴,细细的剐上三千刀,皮肉都尽,方才断首开膛”,“直剁得他做一锅儿肉酱”……手段极其残忍,现在读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再回看张扣扣案,最高法院的复核书也提到:张扣扣连杀三人的做法极其残忍,而且是在除夕这个万家团圆之夜连续杀人,给社会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对于复仇行为,且不说用道德和正义原则来衡量,而且也已经超出了人性的底线,相比于罪大恶极者被杀的那种快意,这种悲剧更值得我们深思。
仇恨本身是“强烈的敌意”,作为一种负面情绪,普遍存在于人类的遗传基因里。小到家庭、邻里纠纷,大到国家、地区之间的战争,无不因仇恨而起。仇恨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让人刻骨铭心、易记难忘;二是难以释怀,甚至终生都难以放下;三有极强的传染性,很容易被模仿。
古代著名的复仇故事无一不是“法外复仇”,缺乏“法”的概念。如果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可以有效减少仇恨犯罪。但是复仇者往往容易主观认为现行的法律是“恶法”,或者对现行的司法体制不信任,认为通过所谓的“合法途径”无法达成所愿,于是“法外复仇”的犯罪动机就容易形成,并被不断地无限放大。一旦形成很难消解,常常表现出目标坚定、破坏力强、杀伤力大的特点。“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逻辑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如果任由其蔓延,很容易从个体的、局部的仇恨犯罪扩展至大面积、大范围的群体性事件。因此,仇恨犯罪更具危险性。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期,更要警惕“仇恨——复仇”的暴力恶性循环,对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威胁。
六、“国家设法,期于止杀”
事实证明,基于宗法伦理的血缘复仇只能使矛盾不断激化,导致双方的冲突极为激烈。因此,统治阶层也很早就意识到,对于血淋淋的复仇,必须加以反对,应该追求忍让、节制的一面,以情感上的抚慰作为伦理上的补偿。
唐代以后,上层统治者更加强调将国法放在礼制之上。唐玄宗说:“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到了唐代,以政府的干预,将复仇纳入法制轨道,对私自复仇进行强制性阻抑,倡导理性复仇,私人复仇之风得以禁止,这种观念得到当时社会主流观念的认同和赞赏。
《唐律•斗讼律》规定,子孙在父母、祖父母遭受殴击的时候,可以回击,但必须有限度。若打死对方,“致死者依常律”,明确指出也要受相应的惩罚,将被处以绞刑或斩首。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前面提到的周智爽,就是现存资料中唐代首例因私自复仇而被处死的案例。
唐律中既肯定了复仇的正义性,又对私人复仇严加禁止,更不用说扩大复仇的范围。 “社会只要认可复仇心,就等于允许人在自己的讼案中自当法官,这正是法律打算防止的事情。” 尽管有少数人认为“替母报仇天经地义”,但是如果国家允许公民个人私自复仇,那么国家的法治秩序就会荡然无存,人类就会退回到古老的“血亲复仇”的蒙昧野蛮时代。纵观历史,无论是血亲复仇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暴力冲突,无一例外不是以悲剧收场,对于当今文明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必须高度警惕复仇文化和复仇思维。
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一些最新的技术正被用于传播最古老的恐惧”。根据2009年5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全球范围内至少有1万个散布仇恨和恐怖主义的网站。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极端分子利用网络散播仇恨,煽动犯罪。在网络上传播仇恨也被称为“网络仇恨”,在这种极端负面情绪的控制下,人们往往会表现为失去理智的行为。
仇恨心理是一种易生成、难排解的心理恶魔,折磨别人更伤害自己。仇恨永远化解不了仇恨,只会导致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玉石俱焚。作为人类原始、朴素的情感,复仇虽有其正义的一面,但若失去理性后果则不堪设想。人类已经走出蛮荒状态,发展到稳定、有序、文明的现代社会,应当摒弃原始、野蛮的复仇思想,通过宽容、理性的文化营造,培育宽容的文化氛围,推崇宽恕情怀,化干戈为玉帛。鼓励合法维权,进行自我情绪的调整与控制。寻求化解和减少仇恨的因素,清除残暴的复仇文化基因,防止悲剧的发生。
法治国家,只能由公权力主持正义,不容许民间私刑复仇。要彻底告别野蛮,应该杜绝无原则的“法外开恩”、“法外处理”,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和稀泥,就会滋长人性中的“恶”。在法治的公正、道义基础之上,分清纠纷、冲突的性质。现代社会的宽容与仁爱,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共同努力。
结语:以法治促进人的自觉自律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刑法只能作用于已然之后,对于社会来说更要防患于未然之前。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要实现人的自觉自律,必须“化性起伪”,用文化、教育等去引导人的自然本性,使之趋向真善美。中国人提倡和表彰符合伦理的道德自觉意识,提倡节制,反对个人的激越行为。中国人的审美心理,难以欣赏那种冲突激烈的尖锐、血淋淋的仇杀和对立,更不鼓励鱼死网破的悲剧。在抗争过程中,以理性控感情,以精神求超越,来满足心灵的慰藉,最大限度地求得团圆。
张扣扣案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撼,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网民抱着“为母复仇”的说法不放,对张扣扣施以“同情”,甚至仅凭主观臆测指责司法的不公。这种现象与认识更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将个人的不幸与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混为一谈,要么是不明真相,要么是无知愚昧,要么是贼德乡愿,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张扣扣的个人遭遇给他的人生带来的极大负面影响,的确令人痛心,但这绝不能成为杀人的正当理由。正如《法制日报》的评论:“不可否认,当前,报复泄愤、私力救济,在一些人中依然很有市场,他们把社会当成江湖,打打杀杀,快意恩仇,自以为是豪侠仗义。”“但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不允许滥用私刑,无论有什么恩怨都不是犯罪的理由。”相比于同情他的不幸,人们更要汲取愿张扣扣案的深刻教训,不能陷入善恶是非不分的泥潭。
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封闭性的社会和传统的相对固定的“圈子”逐步瓦解,每个人都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严守规则与制度。法治体系下需要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科学态度,远离乡愿,大力弘扬理性主义的精神,愿人间不再因暴力而流血,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