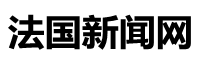本篇文章4104字,读完约10分钟
作者简介:邵光亭,知名学者、经学史专家,书法家、画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教学与传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史学、经学、书法、绘画等,在诸多研究领域皆卓有建树。

狭义的状元特指科举时代进士科的第一名。隋代是我国古代科举制的草创时期,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始建进士科”,但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制度,状元也就无从谈起。唐代的科举制度有常科和制科的分别,由于“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渐渐独尊进士一科。宋代对科考制度进行了若干重大改革,与唐代相比变化极大,开始确立御试制度。北宋初年的科考有州试和省试两级,省试第一即为状元,录取由主司负责。主司多是由皇帝指定的六部尚书或翰林学士担任。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为主司,举人徐士廉状告其取舍不公,取中的进士武济川、刘睿等“材质最陋,对问失次”而被黜落。加上武济川与李昉又是同乡,因此宋太祖大为震怒,亲御讲武殿,“命殿中侍御史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从此殿试遂为常例,形成州试、省试、御试三级科考制度,是中国科举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唐、五代时期的科举考试,主司与举子之间是“恩师”与“门生”的关系。而殿试的确立,使天下进士尽为“天子门生”,作为进士之首的状元,自然也就成为天子最得意的门生。
为了防止权贵干扰和考官徇私,宋朝又采取了保障科举公平的许多有力措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锁院、糊名、誊录、磨勘制。所谓锁院制度,就是在考选期间,考官要与外界隔绝,即便是家人也不得见面。宋太宗淳化三年开始实行“糊名考校”,将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因此又叫弥封、封弥。但问题,糊名之后,考官还可以“认识字画”,通过字迹识别来作弊,故宋真宗根据李夷宾的建议,命专人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再加以复核。这样,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笔迹也无从辨认了。这种制度化的设计,与现在高考的密封制颇为类似。一系列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基本杜绝了“请托”等徇私之弊,状元的录取也越来越严格。从历史上看,宋代状元的质量和整体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很多卓有影响的人物,像吕蒙正、冯京、张九成、张孝祥、王十朋、陈亮、文天祥等,或官至宰相,或为名臣,或为文人志士,皆名留青史,百代敬仰。
辽代初年,状元在礼部试中产生。景福元年实行御试,但规定“进士皆汉人”(《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四,《选举考》),进士科专为汉人而设,状元的录取程序一如宋代。辽代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而所录取的状元则尽是汉人,也是颇为独特的历史现象。
金朝的科考制度与宋代大同小异,其省试有时称会试,最初时也是从中录取状元。正隆二年(1157)御试实行以后,分词赋、经义、策论三科取士,词赋、经义两科针对汉人,策论面向女真人。词赋的第一名为状元,经义的第一名相当于词赋第二名,称为次元。就是说,三科实际上只有两位状元,即汉人的词赋状元和女真人的策论状元。在进士登第授阶方面,策论、词赋科进士第一甲第一名特迁奉直大夫,第二名以下、经义第一名为儒林郎。
元朝的统治制度是“四等人制”,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列为第一等级,其次根据被征服的时间先后,又依次分为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四等人在政治、任职、科举、刑律等方面的待遇均有不同。元代尚右,科举也分右、左两榜,状元从御试中产生,每榜均有两名状元。右榜取蒙古人、色目人,左榜取汉人、南人。相比之下,左榜的考试比右榜多一场,内容也难,录取更严格,考取左榜状元的难度也更大。
到了明朝,科举制发展到顶峰,成为入仕做官的必由之路。考试措施更为严密,科举常规化,定为每三年举行一次。沿袭宋代以来的御试,考场固定的设在奉天殿或文华殿,因而得名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担任主考官,“御笔亲定三名次第”。状元录取后的官方庆祝活动更为隆重,考中状元是举子所达到的荣誉顶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清代的殿试地点改在保和殿,科考制度在明朝的基础上更为详备,从学校设置,到试卷书写的格式、贡院布局的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考试组织分工更具体,会试、殿试的程序繁杂而有序。
进士及第是仕途的起点,而一旦摘取状元的桂冠,更是会迅速赢得巨大声誉,得到最优渥的待遇,为日后仕途的飞黄腾达奠定极为有利的基础。历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鼎甲尤所企望”,但是能不能“状元及第”,除了自身学识文采的因素以外,很多时候还有运气的成分。
按照清代不成文的规定:每逢在位皇帝“万寿及令节”,大臣都要进献贺词。嘉庆皇帝五十寿庆的时候,安徽桐城人龙汝言替某都统汇集了康熙、乾隆二帝的“御诗百韵”,作为祝词和贡品进献。嘉庆大加赞赏,随即赏给龙汝言举人资格,特准“一体会试”,可是龙汝言最终却名落孙山,嘉庆皇帝为此颇不高兴。会试总裁官、内阁大学士董诰从皇帝的近侍那里秘密询问到“今科闱墨不惬上意”的原因,发现就是因为“龙汝言落第耳!”因此到了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殿试,以董诰为首的主考官“仰体上意”,将龙汝言“以一甲一名拟进”。嘉庆皇帝提前偷偷拆开弥封察看,见状元正是龙汝言。结果驾临太和殿宣布录取结果的时候,又假装惊喜地说:“朕果然没看错人”。当时的人流传一句话,说“状元遭际之奇,莫过于龙汝言。”可事实上龙汝言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才华平庸无奇,只是因为喜欢读“先帝”的御制诗篇而被皇帝欣赏录为状元,可最后连《清史稿》都没有为其立《传》。
科举考试的竞争很激烈,闱场逐鹿,成败难料,既有科甲及第的荣耀,也有落第的焦虑与无奈。以明朝为例,宣德七年参试人数与录取人数是16∶1,弘治五年为17∶1,嘉靖十九年为32∶1,嘉靖二十八年达到33∶1。每科乡试之后,除了少量的考生欢喜若狂,更多的是黯然神伤。即便乡试中举,还有更高级别的会试,会试参试人数与录取人数之比有时候也达到20∶1。从表面上看,会试录取率比乡试要高,但会试考生都是经过选拔的,高手云集。有人少年得志,也有人皓首穷经才勉强入围。比如费宏20岁中状元,林大钦22岁中状元,施磐23岁状元及第。成化八年的状元吴宽,11岁为诸生,34岁中举人,38岁才中状元,科举之路走了整整28年。其他如曾彦中状元时54岁,焦竑中状元时50岁。竞争的激烈,不能完全凸显科举考试的复杂性,在同年进士中,有时候年龄差别很大。明朝成化五年的进士中,年龄最小的是江西庐陵人王臣,仅16岁;而年龄最大的奚昌已经49岁;弘治九年进士科,年龄最小的江西新建人王幸卿19岁,年龄最大的浙江兰溪人童品58岁,两人相差39岁。在同一家庭中,弟弟比哥哥先考中,或者父子同时中举,甚至儿子比父亲先考中的情况也不鲜见。如四川新都人杨廷和,成化十四年已经中进士,而他的父亲杨春到了成化十七年才中进士,比他儿子还晚了一科。湖广人氏曾璠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比其子曾省吾(嘉靖三十五年)晚了三科。
科举考试从隋朝创立;唐代定型,宋代以后不断完善,直到明清以八股选士。考试结果可以说是扑朔迷离,结果悬殊、悲喜迥异,令人感慨万千。现实中有人将科举考试视为罪大恶极的教育制度,凡是与科举相关的东西都要大加挞伐。但客观地说,科举制是官员选拔制度,理应由相对客观可操作性的标准,其“应试性”不能完全视之为落后。当然也不可否认,发端于科举制的“状元情结”,对中国人来说可谓是根深蒂固,甚至连为高等学校选拔生源的纯教育活动——高考,也异化成“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活动。“状元”一词,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陈腐的气息,实际上是成了“做官发财、一步登天”的代名词。
今天的“应试教育”不是科举制造成的,更深层的,是教育竞争的结果。“每时每刻的竞争和焦虑不安的心理”,使得教育供给与理性的教育需求之间严重失衡,导致教育竞争过度。
“状元崇拜”与“证书主义”、“文凭至上”一样,推动教育竞争变得更加无序,背离了教育目的。考试的本意是因为教育资源有限,而不得不采取的资源分配方式,但如果是考试变得至高无上,甚至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则考试不仅左右了学的目的,也左右了教的目的,成为与教育的本义相对立的活动。
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社会是“甲天下”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是皇帝的私产,天下万民也都是皇帝的“子民”。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中,看着士子们鱼贯而入,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封建帝王对于人才的态度,也道出了科举制的真谛,就是将人才纳入到体制中来,为我所用。从这个角度看,科举制就是个笼络人才、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包括状元在内的知识分子都是“工具人”。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德治和教化,首先是以维护封建等级制为目的的手段,无视人的自身价值和个性特征并不奇怪。
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制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通过考试来决定某种机会,因此都存在功利性。但是这两种机会的性质却有本质区别,科举通过考试决定的是能否获得功名和入仕做官的机会,是寻求封建特权的对结果有明确预期的活动,一旦考中,特别是高中状元,也就意味着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两方面都可以获得质的改变,并不单纯只是一种教育制度。而高考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决定的只是升学机会,获得的充其量只是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改变的可能。即便是通过高考获得某种文凭,事实上也不意味着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就一定具有优势。“学历崇拜”不是由教育制度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用人制度决定的。
作为长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的国家,对于考试优胜者的羡慕和追捧,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与“高考状元”相关的种种盛况,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集体意识的遗续。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高考也和其他任何一种考试一样,仅仅只是一场普通的考试,仅此而已。炒作“高考状元”,不仅有宣扬应试教育的嫌疑,更重要的是,这一“状元”头衔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反而容易让学生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对身心健康也极为不利。
鲁迅先生说:捧杀比棒杀更厉害。捧杀与棒杀,都是中国人世俗风情中的景观。“高考状元”表面看来是对年轻学子、青年才俊的追捧,背后的逻辑实则是教育的功利化、商业化。大搞“状元”崇拜,不如大力弘扬刻苦的意志、远大的志向和追求理想的信念,在全社会营造热爱学习、尊重人才的氛围。诚如是,则国家民族伟大复兴便指日可待。